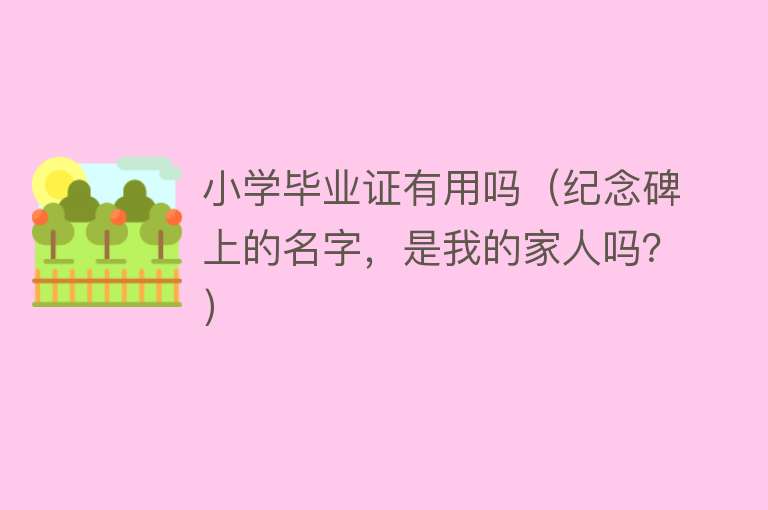
现在,所有人都老了,有的人已经去世。
风烛残年的老人走在人生最后的路途上。眼下,71岁的崔秋荣越来越焦急难安,皱纹像一个兵团一样,将它的领地征服,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多年来,她和家人一直在证明抚顺市儿童公园人民烈士纪念碑上一个名字的错误。平静下来时,崔秋荣才意识到,已经六年过去了。
烈士碑上的名字。
崔秋荣一家漫长的证明之路,始于烈士碑上面的一个名字。
2017年,她的哥哥患癌病重,她从北京工作的茶馆请假,回抚顺照顾他。几个月后,哥哥去世。没多久,她在辽阳的姐姐崔春安和姐夫张国有回了趟抚顺。
到抚顺后,张国有和妻子住在崔秋荣家里。一天晚饭后,他们出门沿街散步,三个人嘴上没说,不约而同往一公里外的儿童公园走。
公园里有一座烈士纪念碑,在他们的共同记忆里,碑上刻着张国有父亲张鹤泽的名字。根据《抚顺市志》记载,这座人民烈士纪念碑高19.8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镶嵌着大理石板。1949年11月修建时,上面刻有144名抚顺烈士的姓名,经过1962年、1975年、1992年、2022年四次维修。
那年张国有78岁,他的脚脖子摔折过,走路不便,但到了公园,他几步迈上阶梯。崔秋荣姐妹俩还在石阶下面时,突然听到张国有在碑前喊起来:“我爸这名字怎么还错了?怎么变成铎了?”他上一次见到碑上父亲的名字还是在中学时期。
听到姐夫的喊声,崔秋荣也跑了上去。张国有指着碑上的第一个名字,皱着眉,脸色沉下来,不断重复,“这名字怎么还弄错了呢?部队番号也错了,应该是126师啊。”他几乎是吼出来的。这块碑上写着:张鹤铎:抚顺市人,志愿军二十六师参谋,一九五〇於抗美援朝战斗中光荣牺牲。
崔秋荣安抚他说,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她寻思,改日上有关部门把这事儿一说,一调档案,不就给改了吗?
回家以后,张国有继续阴沉着脸,心脏的毛病又犯了,总心慌害怕,崔秋荣姐妹俩想出去买菜,不敢把他一个人扔家里。
这对夫妇有两个孩子,大儿子11年前食管癌去世后,只剩下二儿子张乾。张乾今年56岁,平时要照顾下身瘫痪的妻子。加上他们一家人早年随工厂迁到辽阳定居,往返不便,更正名字的任务就落到崔秋荣身上。
当时,崔秋荣正在北京的一家茶馆里工作,她先是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但最初反映情况后没有结果。为了办好这件事,崔秋荣从北京辞掉工作,搬回了抚顺。
在张鹤泽留下的这张泛黄的照片上,他身着戎装,双手交叉在一件无法辨别的物品上,坐在凳子上,模样清晰可辨。照片背后写着“一九五九年八月”,据崔春安回忆,这是当年她和张国有确定恋爱关系,张国有的母亲刘桂英把照片交给她时,她写下的字。在结婚后,她又在背后写下“张鹤泽”三个字。这张照片一直收藏在箱子里,2017年,崔春安才翻箱倒柜把它找出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遗物。
张鹤泽的照片和崔春安在背面写的字。
证明父亲是父亲。
那时崔秋荣不知道,要证明一件发生在70多年的事,远比她想象中艰难。
2017年,崔秋荣开始找抚顺市--要求调出张鹤泽的档案,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2020年,抗美援朝烈士遗骸回国那天,她看到电视里的直播画面,心里一沉。家人等了多年,一直没有张鹤泽遗骸的消息。“就烈士碑上留这么一个名字,那是一条人命。”她一拍大腿,从沙发上站起来,心里想,这件事必须得有个结果。
张国有在病床上写委托书给崔秋荣。
在她提供的录音内容中,局长听完她的讲述后说,“你怎么能证明张鹤泽就是张国有的爸爸呢?”
局长说,“你还用跑那么远吗?调烈士儿子的个人档案不就行了吗?”
崔秋荣一拍大腿,说,“行,就这样。”
这之后,张乾在辽阳调取他父亲张国有的档案,崔秋荣在抚顺调刘桂英的档案。
张国有的档案里关于“生父张鹤泽”的记录。
几天后,她把档案材料拿到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但没人收材料,要求她提供“直接证据”,即一本烈士证。
崔秋荣说,烈士去世后,当时有两名军人护送烈士妻子刘桂英回抚顺,带着张鹤泽的所有档案,烈士证、光荣证之前一直在刘桂英那里保存着。但时间过去太久了,刘桂英也已去世40年了,目前他们家里已经找不到这个证件。
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部监制的“光荣之家”
老人回忆,那个送材料无果的晚上,她梦到自己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述给主席听,主席听后发话,让下面的人解决好这件事。她把这个梦看成一个好的征兆,于是就去北京了。
崔秋荣--军人事务部交完材料,她从北京坐火车回抚顺。傍晚的车站不再空空荡荡,穿戴整齐的男人和女人排着长队等待火车,熙来攘往。她坐在椅子上,回味那两年的经历,忘记自己已经快70岁了。
从北京回来后,崔秋荣拎着一摞材料到抚顺市军人事务局的权益科,接着又跑到市里一个军区,她把材料交给了一名姓贾的干事。
等待一直没有结果,她决定收集更多的证据。她先是去找了以前住在一个院里的邻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邻居住在刘桂英隔壁,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经常一群孩子围着,坐一起唠嗑。
2021年8月21日,崔秋荣找到这个邻居时,老人已经78岁。崔秋荣和她说明来意,老人说,“好,我知道了。”老人转身进屋后,因为疫情不方便进屋,崔秋荣一直在门口等着。一个小时后,老人递给她一张按了手印的手写证明纸条。
事隔两年后,前不久,崔秋荣再次来到老人家门口,她看门上没贴对联,心里慌乱,有不好的预感。后来得知,老人已经去世了。
崔秋荣写的日记。
档案和人的记忆。
在崔秋荣搜集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里,她认为“一份有力的证据”是张鹤泽妻子刘桂英的档案。她清楚记得那天是2022年9月18号,天下着大雨,她跑到市里的档案馆,哀求工作人员把刘桂英的档案给她看看。
第一次吃了“闭门羹”她让崔春安从辽阳寄给她一份委托书,第二次去她才看到了刘桂英的档案。在刘桂英的个人的档案里,记录着她于“1946年至1952年随爱人参军在部队托所保育员……刘桂英同志是1952年由丹东部队42军126师转来我厂的……刘的爱人是参谋,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刘本人是后勤部的保姆,也是解放军战士。”
第三次是去年12月15号,崔秋荣到档案馆,疫情刚放开,街上空无一人。她把刘桂英档案里面的工人登记簿找了出来。在这本陈旧泛黄的册子上写着:烈属刘桂英是新户部队来的,她是从丹东部队过来的。当她看到“烈属”两个字时,她高兴得心脏快要蹦出来,因为“拿到一个重要的新证据”
刘桂英个人档案里的材料。
刘桂英和张鹤泽只有张国有一个儿子,原名叫张喜胜,但父亲去世后,126师的首长将他改名,“归国家所有的意思”他生于1940年,从武汉的中学毕业时,他16岁。从他的--上可以看出,他毕业于武汉军区东湖八一小学。
张国有也曾参军入伍,在大连旅顺服役声呐兵一年九个月。退役后,1963年,他被分配到抚顺发电厂工作。在一份张国有填写于1977年1月16日的工人登记表里,写着“生父张鹤泽,50年在抗美援朝战争牺牲。”同时,在详细履历中写着“49-53,随军家属”
另一份是资料是崔春安写于1965年10月6日的证实材料,那年她25岁。在这则材料里,留着她当年的蓝色钢笔字迹:“父亲张鹤泽,解放前大约在1944年左右参加解放军,在部队担任师参谋。在1950年在朝鲜战场光荣地牺牲了。”
崔春安个人档案里的记录。
1975年,张国有带着家人,跟着工厂迁移到辽阳定居。一晃几十年过去。张国有不能再像六年前一样,箭步冲到烈士纪念碑前。如今他头发全白,戴着一副易碎的眼镜,躺在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胸痛中心的病床上。
刘桂英去世时,崔秋荣30岁。当她翻看那份尘封已久的档案时,遥远的记忆涌出来。她家和刘桂英家住在相邻的两栋楼里,那里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电厂的工人住宅。去工厂上班后,她时常把孩子放到刘桂英那里。老人喜欢吃饺子,许多个中午,她擀面皮做好饺子后,给住六楼的刘桂英端上去。
2021年之后,崔秋荣相继找到三名邻居和张国有的一个同学作证张鹤泽是烈士。在东北的工人家属楼里,孩子们从小在一个院里长大,邻里之间的事彼此都知道。
据证人们说,张国有有一个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父亲,他的名字被刻在西郊公园的墓碑上。小时候,他们入少先队时,去公园参观过,也去过张国有家,多次听老人讲过这些故事:张鹤泽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担任42军126师参谋,在完成一次侦察任务时,乘坐吉普车的一行四人遭遇美军的炮弹袭击光荣牺牲,四人无一幸存。
证人的证明材料。
知道张鹤泽73年前战时事迹的人,许多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崔秋荣提交材料时,她担心工作人员弄不清人物关系,又另外制作一份表格,把人物的简介列出来。在一些重点句子下,她用红色的线条勾勒出来。
无数张证明材料像地毯一样铺在眼前,越到后面,崔秋荣意念越强:要给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
又一次回到起点。
多年等待后,今年2月28日,崔秋荣收到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份电子回复,工作人员直接在微信上发给她的。
崔秋荣2月28日收到的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给她的答复。
这份回复还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派人前往市社科院查阅《抚顺市志》。《抚顺市志》市情要览卷明确记载为“张鹤铎,抚顺市人,志愿军二十六师参谋,一九五〇年于抗美援朝战斗中光荣牺牲”,与烈士纪念碑一致。
收到这两封迟来的回函时,崔秋荣感觉自己像一只陀螺,转了无数圈后,又一次回到起点。从那以后,她晚上失眠,不知道从何着手。
崔秋荣买过《抚顺市志》,前后看了三四遍。在这本《市志》中,有两份烈士名单,一份有1900余名烈士信息,另一份记载了130余名英烈的情况,后者被镌刻在人民烈士纪念碑上。
崔秋荣发现烈士碑上和《抚顺市志》上疑似错误之处。
6月15日,带着这些疑问,崔秋荣再次来到抚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她提交这些证据的基础上,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王俊告诉她,应该去军区查找有没有张鹤泽的记录。
崔秋荣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只要有蛛丝马迹,她会揪住不放。这件事情的困难之处在于:她提供了所有她能提供的证据,但最后被否定了。
就在她绝望地等待的时候,张国有再次被送进医院抢救室。她不知道在多久以后,调查会出来结果。
崔秋荣感觉自己像掉进一个齿轮里面,出不来了。她想继续做些什么,却又不知道做什么好。
烈士碑上张鹤铎的记录。
至少还有一个名字。
距离王俊说的调查过去十八天后,崔秋荣决定亲自去退役军人事务局问问情况。去的那天,她起了个大早,喝了杯咖啡,吃一个鸡蛋,吞下几粒药丸,烧了三炷香,又跪下,磕了三个头,才出门。
如今距离张国有发现父亲名字“错误”已经过去六年,他还在等一个答案。而在张国有看来,要改掉这个错误的名字,应该是一件小事。他始终不明白,“这件小事”为什么变得这么难。
有时他一生气,就像小孩儿一样哭着嚷着要跳楼,妻子吓得直哭。后面几年,崔秋荣做这一切的时候,都瞒着张国有。因为她知道姐夫的健康正在急速衰退,每次他问起来,家人只说还在等回复。那时,他只会长长叹气,从前几年的声音急躁有力,到后面越来越弱。
崔秋荣10岁时,母亲在工厂上班,一只脚踩进灶坑里,闪到腰,不能站不能蹲,仍在工厂扛重东西,哈腰给孩子们切挂面,到去世时腰也一直弯着。崔秋荣心里不服,要求认定母亲为工伤。她记得自己写了书面材料,但最后还是没成。她说,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对的事情一定要坚持。
十多年前,崔秋荣的女儿在下班回家爬楼时,被人拿刀刺穿了手臂和肺部,二楼到五楼的阶梯上留下血迹,那栋楼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女儿留下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崔秋荣一直想找到凶手。现在,她不敢在黑夜下楼。而白天上楼时,能看到阶梯上残留的血迹,她说当时她用肥皂水清洗过,但没洗干净,等张鹤泽的名字改回来后,她要再清洗一遍。
眼下,崔秋荣有两个心愿,希望姐夫张国有能活得久一点,以及错误的名字能尽快改过来。至于为何执着于这件事,她认为是内心的良知在呼唤和一种承诺,自己只是在证明一个人存在过。
崔秋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她的头发全部整齐盘在后面,额角露出几根白发,说话时声音清澈有力。2005年和丈夫离婚以后,她一直是孤身一人,家里的线路、水泵、马桶、水龙头,都是她自己安装。
邻居有困难,她也经常帮忙。从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家路上,在小区楼下碰到两个邻居,说五楼窗台上放了一盆水仙花,快死了,让崔秋荣救救它。上了楼,崔秋荣看了一眼,花已经淹死了。她家住在八楼,没有电梯,她膝盖不好,爬几步楼梯,要停下来歇歇,再爬。
尽管体力不如以前,崔秋荣仍然精力充沛且灵活。在家里,她整日坐在客厅一角的椅子上,一遍一遍地翻看有关军人记录的书籍。有时早上煮熟的鸡蛋,到了晚上才记起来吃一口。长时间盯着书和手机看,她视力下降许多,在抬头的一瞬间,眼前一切是模糊的。
6月的最后一天,带着关节炎病痛和心脏不适,崔秋荣再次来到儿童公园的纪念碑前。公园一侧的林荫道下,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一个穿浅蓝色条纹衬衣的老人站在纪念碑前,盯着一个叫“刘迪”的名字看了很久,脸上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崔秋荣问他,你有家人在上面吗?
“有,这是我姑婶儿的爸爸。”老人用手指了那个名字,脸上笑容荡开,眼神里有种欣慰。“你也有家人在上面吗?”老人问。
“我家人的名字给弄错了。”说完,崔秋荣停了下来,神色变得遥远,声音又有了那种哽咽。这六年带走了很多她的东西,她自己的生活,她一直坚信的事实,以及在一次次试图证明这些事实时的期待。